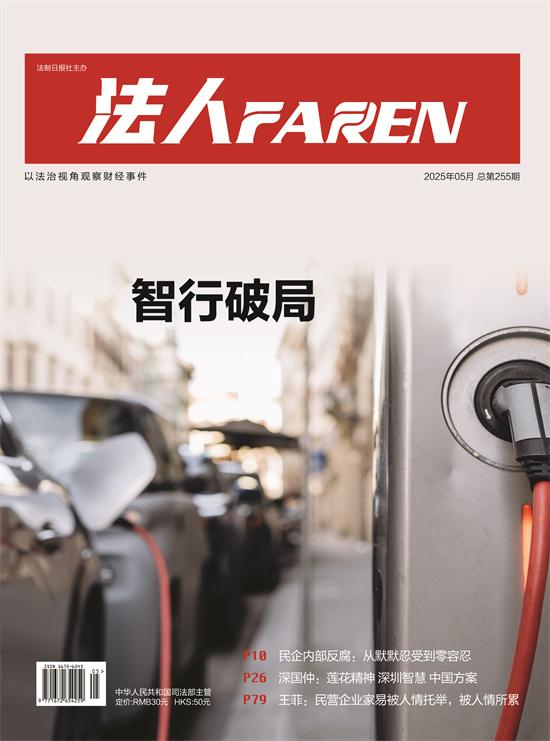文 《法人》杂志全媒体记者 王茜
可监测心率的手表、加热披肩暖身毯子、可以发声的点读笔······随着技术创新和商品迭代,市场上出现很多复合型新兴产品。当其功能横跨多个传统类别时,如何界定这些商品的属性以及如何将它们正确分类,关系到企业在进行商标申请时是否面临被驳回的风险。

▲CFP
当前,商品区分方式存在的分类逻辑问题已引起业内人士广泛关注。为避免商标冲突,亟须适时解决分类标准多元、具体商品/服务名称粗细不一、类别重复等问题。
模糊分类易引发商标对垒
“这款手表不仅具有日常通讯功能,还可以监测心率、记录运动。它应该归类于电子通讯设备还是医疗器械?”某电子产品开发企业法务总监问《法人》记者。
某科技公司研发一款兼具家用安防和可穿戴监测功能的多合一设备,由于尚无专门分类,企业勉强选择“家用电器”类别注册商标,但另在“监测仪器及设备”类别已拥有商标的企业如提出异议或起诉,指称“跨类别侵权”或“混淆近似”,该企业可能面临商标侵权诉讼。
上述法务总监指出,商品不断迭代,市场存在很多本身具有复合型的新兴产品,当其功能横跨多个传统类别时,竞争对手或其他市场主体可能已在其中某个类别拥有注册商标,由于分类不匹配,企业的新产品容易被认定与已有产品“高度相似”,从而引发纠纷。
记者注意到,模糊的商品和服务分类增加了企业商标申请被驳回的风险,导致企业需要在多个类别“多头申报”,不但企业注册成本和管理压力大幅上升,而且可能对企业的长期品牌资产造成冲击。
“当前商品区分方式存在的分类逻辑问题,如分类标准多元、具体商品/服务名称粗细不一、类别重复等,需要进一步厘清和解决。”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技术创新的迅猛发展促使产品形态快速迭代更新,《类似商品与服务区分表》(以下简称“区分表”)难以适应新型产品的界定需求,无疑加剧了商标冲突的复杂性。以电子产品为例,其功能集成度不断提高,在商标授权确权,尤其是侵权纠纷中,准确判断相关产品类别变得极为困难。
区分表是原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以及中国自1988年11月1日起采用国际分类以来的使用实践,针对中国国情实际对商品和服务的类似群组及商品和服务的名称进行翻译、调整、增补和删减而制定。此后,该分类表亦随着国际分类表的修订而作相应调整。
“商标归类错误易导致企业在商标纠纷中,面临更加复杂的诉讼过程。”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叶菊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亟须对非规范商品的归类争议予以回应。
“针对功能聚合类商品,需结合具体聚合方式(如相近功能整合、技术升级、复合功能)及不同程序(侵权、驳回复审、无效宣告)中的利益平衡,灵活调整判定标准。”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杜颖表示。
品牌被“蹭用”后的维权战
“爱国者”商标案可谓为涉及商品分类问题的典型案例。
时间回到2005年。自智能手机诞生后,为让手机更薄更美观,内置电池的设计逐渐成为主流,但由于内置电池容量有限,移动电源开始出现。爱国者公司最早于2005年涉足移动电源产品,是最先加入该产业的企业。不过在2014年,市场上出现了飞毛腿公司生产的“Patriot爱国者”的移动电源产品。该产品在外包装上,以类似“爱国者集团”“爱国者公司”自称,并以“爱国者集团监制”等字样进行宣传,同时在电商平台以拥有此商标为由,要求对“aigo爱国者”产品下架。随后,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商标权归属案拉开序幕。而这场“诉讼拉锯战”又被喻为中国品牌的“海湾战争”。
爱国者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993年的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aigo爱国者”品牌在中国具有较高知名度,2006年即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飞毛腿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于1996年7月16日申请“爱国者”文字商标,核定注册在第0922组“电池充电器、电池”等商品上。爱国者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于1996年9月6日申请“爱国者”文字商标,核定注册在第0901组“计算机、计算机周边设备”等商品上,并于2006年、2012年、2014年、2015年在移动硬盘和闪存盘(计算机周边设备)商品上相继被商标局、商评委、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驰名商标。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员陈锦川对此案分析称,引发两者进行商标对垒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被告申请注册商标时,其核定使用的产品不包含移动电源分类项目。“当时,市场上没有移动电源类商品,相关产业界也未出现此类别商品概念。原告自2005年起将其注册商标使用于移动电源产品上。被告虽提交了2010年与移动电源产品相关的合同,但并未提交实际使用的证据。2015年,区分表新增‘移动电源’商品,并将其划入0922群组,与电池、电池充电器属同类相。”
“被告申请注册商标时,无法预见移动电源会出现在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中,依据近20年后的区分表,认定被告对10年后才出现移动电源的使用在其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属于其注册商标权保护范围,与事实严重不符。”陈锦川认为,原告的商标早在2006年即为驰名商标,且2005年就率先在移动电源上使用,已在相关市场产生并积累了归属于原告的商品声誉,成为既有市场的占有者,其商誉及产业扩张中的利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当前,随着技术发展和产业融合,市场上出现的大量新兴产品,在区分表中难以匹配相应的类别,或可能找到多个类似的商品。据记者观察,当前企业面临的商标风险,呈现出与传统商标侵权不同的复杂态势。过去常见的“蹭名牌、搭便车”等商标侵权行为,界限相对清晰、判断标准也基本统一。但当前,商标纠纷双方常常各执一词,且各有理由。
“友宝”商标侵权纠纷案中,原被告的争议焦点也在于“类别不同”。原告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投币启动设备用机械装置”,而被诉侵权商品为“智能快件”。被告辩称,其在第6类“金属箱”商品项下,与原告的商标使用商品不构成类似。
叶菊芬认为,因商品社会属性交叉、重合而类似,虽然在区分表中属于不同大类或不同类似群组,但根据具体交易实际情况,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高度重合或交叉,再考虑权利商标的显著性、知名度等因素,认定构成类似商品。类似商品的认定应当更加关注商品的社会属性,而非商品的自然属性,即应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一般认识来判断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
商品与服务的“类似”认定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软件即服务(SAAS)、加密货币服务等新形态产品和服务,传统尼斯分类体系无法完全涵盖。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产品功能和用途,还模糊了商品和服务之间的概念,促使分类调整成为必然。在互联网创新背景下,互联网与金融、教育、交通、医疗等产业跨界融合,并以APP作为提供服务的主要接口。商标使用权利的界定,呈现更加复杂的状态。
以“钱包理财”商标侵权纠纷案为例,被告经营“钱包理财”APP,原告“钱包”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包括第9类计算机程序。法院认为,被告虽然要求客户在手机上安装使用APP程序,但提供服务的内容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仍然是金融理财服务,只是服务场所转移到互联网平台,故认定系在金融理财服务上使用被诉商标,而非在新产业扩张中的第9类商品上使用。同时,法院还认定不构成商品与服务的类似。
叶菊芬对记者表示,从形式上看,APP属于计算机软件的一种,属第9类商品范畴。但实践中,大量案件并未将“提供某一名称APP的行为”认定为在计算机案件商品上使用商标。
“在数字商品和服务类别更新方面,其主要集中在软件应用、数字内容和在线平台领域。例如,音乐流媒体、电子书等数字内容传输的扩大,促使引入新的子类别。”河北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张晓梅表示。
叶菊芬还认为,商品和服务在区分表中属于不同类别,且没有类似或交叉检索关系,一旦认定类似,也是一种“突破”。如车辆维修服务与汽车清洗液商品、餐馆服务与调味品商品等。如果商品是提供服务的必用或常用物品,则二者的服务或销售场所、消费对象相同,以相关公众的一般交易观念和通常认识,容易误认为由同一主体提供或具有特定联系,可认定构成商品和服务的类似。对于不存在以上固定联系,仅因服务提供者的使用而产生关联的服务用品,一般不认定构成商品和服务的类似。如快递服务与衣服、腰包、头盔等骑手装备。
“司法实践中,应以区分表为起点,准确认定商品或服务类别,遵循 ‘谁主张,谁举证’ 原则,结合使用场景、商标知名度、主观恶意等因素,以避免混淆为核心,判断是否类似,既尊重分类逻辑又兼顾市场实际,平衡商标保护与公平竞争。”叶菊芬表示。
责编|白 馗
编审|渠 洋
校对|张 波 张雪慧